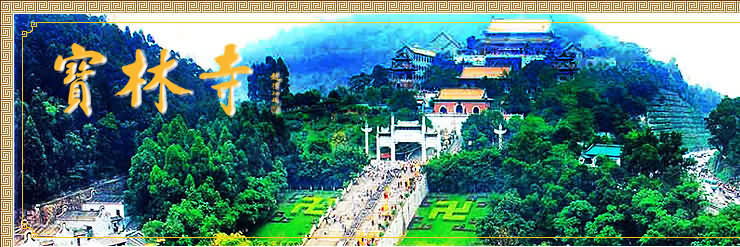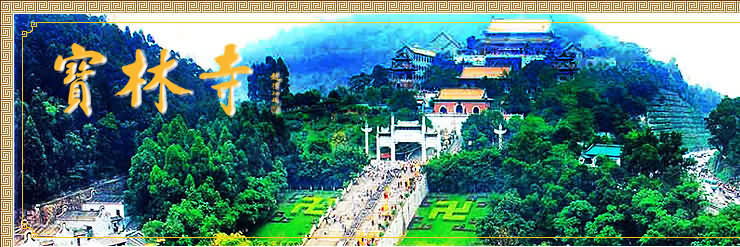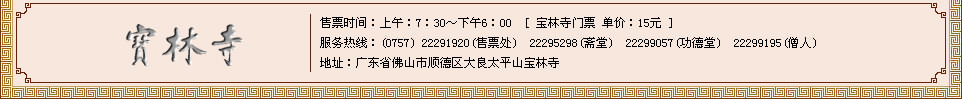福
文\一苇
如果问一个中国人最想得到的字是什么,回答最多的一定是这个福字。
从古至今,从生到死,这个福字一直是我们所追求的。
那么你幸福吗?
福,可以分拆为“示”和“畐”。示,就是供案;畐,古文字中其实是一坛老酒。“示”和“畐”结合起来,意思很简单,把这坛老酒献出来,而不是留下自己独饮。
现在也有人把“畐”形象地拆解为“一口田”,这正是对福字的一种理解,或者说一种态度,一口田,就是幸福。幸福原来只需要这么一点点。
和畐字相关的字,还有一个最常见的同样也是颇受人青睐的 “富”字。上面宝盖的古义就是房子、家的意思。富字就是把这坛老酒摆在家里。古时只有在粮食有剩余的时候,才会拿来酿酒,所以如果你家里有酒,多半就有余粮,那么一定就是富人了。
汉字之所以有如此魅力,正在于它的奥妙无穷。看看这两个字的禅机:不论这个畐字你把它理解为一口田,还是一坛酒,如果你把它放在家里,那么你得到的只是“富”而已。如果你把它献出来,那么你得到的就是“福”。福和富的差别就在这里。只要是你诚心所献,千口田是福,一口田也是福;陈年佳酿是福,二锅头也是福。
《佛说四十二章经》上说:
佛言:睹人施道,助之欢喜,得福甚大。
沙门问曰:此福尽乎?
佛言:譬如一炬之火,数百千人,各以炬来分取,熟食除冥,此炬如故。福亦如之。
福的复制和分享,带来的只能是更大的福,而不是失去。
结语:福,不管你手里捧的是什么,把它献出来。数百千人的火炬点亮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幸福就是你的影子。
利
地里的庄稼熟了,农民手拿镰刀,收割田中的庄稼,收获的喜悦洋溢在眉梢。这就是利字为我们描摹的场景。
一把成熟的嘉禾,一把闪亮的镰刀,组成了这个利字。
利是什么?用刀去收获。
功名利禄,人生的四大追求目标,其中之一就是利。
世人讲求一个利,常常有两个问题搞不懂。
一是你拿着刀去收获,割来的庄稼是自己种的还是别人地里的?
二是你收获的是什么,你看清了吗?
如果你割了别人的庄稼,这样的利或许早晚会走向它的反面。如果你还没看清是什么,就下了刀割回家,哪里知道是福还是祸?
所以下手之前,三思而后行。
利的另一意向是锋利的利,“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的利。
所以追逐“利”的时候,小心割破了手。
佛家有没有利?佛家也言利,是“自利而利他”的利。
此利乃大利。如《药师本愿经》中所说:“此言闻说药师名号,本愿功德,依之修习,即可拔除一切业障,得大利益安乐。”
此大利益到底是什么?
且回头再看看这个利字是什么。
一把嘉禾一把刀。禾是什么?禾是你看到的。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看到的是相,是虚妄的相。这把刀是我佛赐予你的,割掉这个相,则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结语:利,一把嘉禾一把刀。你果真割到什么了吗?
药(藥)
药(藥)无上古字,或始于汉。但“藥”下的“樂”(简体“乐”)字则古有之,比如金文,比如甲骨文。金文中今字的要素已经齐备,底下为木,象乐器之木质基座,如琴如瑟;上部左右为丝,象琴弦;中间的“白”字其实是大拇指,象以指弹琴。
樂字活脱一幅抚琴图。
看来在古人那里,抚琴听琴乃人生最大之乐事。
不幸的是人生更多的不是快乐,而是痛苦。有肉体的病痛,更有精神的病痛。于是我们的先人就开始寻找医治病痛的办法。
大概是神农吧,他徜徉在草丛中,一筹莫展之后,突然醒悟所有医治病痛的办法其实就在脚下。尝过百草,于是就有了医治百病的药。
抓来一把草,还给你快乐。这就药(藥)。
有一则文殊菩萨的故事:
文殊菩萨一日令善财采药,曰:是药者采将来。善财遍观大地,无不是药。却来白曰:无有不是药者。殊曰:是药者采将来。善财遂于地上拈一茎草,度于文殊。文殊接得,呈起示众曰:此药亦能杀人,亦能活人。
药,能还给你快乐吗?如果是,药同样也可以还给你痛苦。尤其是今日之嗑药族,把药的含义诠释得淋漓尽致。一撮白粉,它能带给你极致的快乐,同时也一步步把你推向深渊。
病因不同,药量不同,配伍不同,甚或目的不同,药能活人,亦能杀人。
还有,自古以来,多少人间帝王,一直在寻找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却多半因此而葬送了性命。
人间真的有灵丹妙药吗?有,药师琉璃佛手中拿的就是。
药师佛手中拿的是什么,你看清楚了吗?
结语:药(藥),草丛中的琴声。你能抓来一把琴声让我看看吗?
宁
慧可问达摩:“诸佛法印,您可以教我吗?”
达摩说:“诸佛法印,不是跟人学来的。”
慧可又说:“我心未宁,请您使它安宁。”
达摩说:“那好,你把心拿来,我设法让它安宁。”
过了许久,慧可说:“找了半天,没找到心在何处。”
达摩说:“好了,你要我设法安宁你的心,我已经做完了。”
宁,本字作寧。
最上为房子;下面是心;再下是皿,古字乃古代盛器豆的象形,功能相当于今天的盘子;最底下的丁字或是案子的象形。
宁,就是把房子里的一颗心放在案子上的盘子中。
宁,安宁,宁静,是喧嚣世界里的一种奢望,是现代人所久违了的。在如今的尘俗世界里,就像这个简化了的宁字,丁是人丁,代表着一个人,即使这个人闷在屋子里,也找不到自己的心和能放下心的那个盘子。那颗心哪里去了?迷失了。那只盘子哪里去了?丢失了。
然而,宁字的简化告诉我们的不止是这些,它还讲述了上面那个宁心的故事。达摩对慧可说:“你把心拿来。”于是慧可这才发现房子里面没有这颗不安的心,就连本可以盛下这颗心的盘子其实也找不到。这就是无心心自安。
这个宁字的演变真是充满了禅机。最早的甲骨文,本没有上面的房子,可见古人即使没有处在房子之中,依然可以宁。也许是后代的人,做不到这一点,于是在心上扣了一个房顶,以隔绝外界的喧嚣。境界自然是低了一等。
宁字还有一种写法,是心字下为用字。用心则宁。用心投入地做一件事情,的确可以让人安静,除用心之事外,旁若无物。这也是一种宁,比如用心读书,用心禅定。但毕竟是用心于某事,如无某事,则又难得安宁。境界自然又低了一等。
那么,我们可以排一个有趣的顺序,看宁字的境界,由低到高吧:
宁——甯——寧——甲骨文宁字(无房子,不惟无房,其实也没有房中之心)——宁
转了一圈,又转了回去。
结语:宁,放下你的心。如果你攥着它四顾找不到放下的地方,就松开你的手吧。
我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
繁星满天,银河横亘,我常常仰卧在草垛上,和许多人一样在想。却越想就越想不明白。
后来我又在想,古人造得我字,也是一个奇怪的事。这个我字,究竟从哪里渊源,又想说些什么?
甲骨文之我字,是一个兵器的象形,通俗讲,就是一柄带齿的大斧。而《说文》说:“我,古杀字。”这个我字,究竟要杀什么?
佛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我相即是非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是非相。
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中,根本乃我相,若无我相,何以有人相、众生相、寿者相?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而我相是诸相中的根本相,所有烦恼的根源都来自于执着于我相。所以我们终于明白,我,这柄带齿的大斧要杀什么?杀我相,就连我相中的沟沟坎坎,也由于这斧刃上的齿砍得干干净净。
“我”之意识是造化赋予一切生灵的禀性,有了“我”之意识,才有了保护自我生命的意识,才会饥则食,渴则饮,生命才能存续。这本是一种自然状态,但在物欲横流、眼花缭乱的现实世界里,这种自我意识膨胀,异化,多少可怜的人抱定我相不肯撒手,于是生出一波又一波不尽的烦恼。
那么这个我,究竟有还是没有?被世人所执着的我相、八大自在的真我,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哪个是有,哪个是无?
如果你挥起这柄带齿的大斧,一斧子下去,一切迎刃而解。
繁星满天,银河横亘,我常常仰卧在草垛上,和许多人一样在想。看河汉之迢递,天地之间,我不过是草垛之上的一粒微尘,何不运斤削垩,还原本心。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
我,谁也不是。我从来处来,到去处去。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
结语:我,你要寻找自我吗?运动你的斧子,不留一丝余地,一斧子砍下去,剩下的就是了。
净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净字,本身有它传奇的历程。跟随它,回溯它的轨迹,或许也是一条心灵回归之路。
净,以往多写作浄。而净,多用在“冷”的意向中。
浄的本义又是什么呢?《说文》解释说:“鲁北城门池也。”段注则说的更为详尽:“其门曰争门,则其池曰浄。”可见因为城门叫争,则争门的水池加上水的偏旁,就是浄了。这个浄字,和纯净的含义毫不相干。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浄字何以又成了纯浄的浄了呢?原来古时亦常用简化字,在文字学上被称作俗字,就是民间习用的字。而这个浄字就是古俗字,被借来用作替代另外一个更难写的字,这个字就是瀞字。瀞,才是纯净含义上的净的本原字。
水静则瀞。溯源至此,我们终于找到了净的本义。这也是古时净静常常被互用的原因。风浪中的水尘沙翻涌,混浊不明,只有等到风平浪静,尘沙沉淀,才能显出水的澈净。
水如此,心亦如此。耳闻目睹,所有烦恼,其实都是心中被色受想行识的风浪扰动的尘沙。如果拨开五蕴的假象,水自平静,自然还原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的自性清净心。
既然水静为净,那么我们再来品味一下这个静字。静,由青争组成。青,是一种颜色,上古字上半部为生字,象植物之生长;下半部为丹字,象矿井中采朱砂之形。青红,为木火之色,这里有五行生克五行轮回的含义,暂且不及详述。争,本写作爭,乃两手相争之形。二字相拼,仍看不出安静的含义。那么这个静的含义是怎么来的呢?看一下墙盘上的铭文,静字被写作青,而在上古字中清同样可写作青,所以,组成静字的青,其实是清的意思。于是我们发现,静字的含义也是瀞。用清的方式让争停下来,这就是静。注入一泓清水,洗净争夺心,就可以得到我们向往的宁静。
再回到净。净是什么,站在原地,就字论字,左边的两点水是冰,右边是争。让争夺冷静,冰冻,争夺没有了,一切都会变得纯净。那颗自性清净心也会被我们重新发现。
结语:净,如果把两只争夺的手变成同一个人的手,那么,请合起你的掌来,念一声阿弥陀佛。
淡
淅淅沥沥的秋雨下了一天,没有丝毫雨住的迹象。久违了天高云淡,皓月当空的中秋之夜,而且今晚恐怕仍不得见了。
伫立窗前,看雨打水面的闪动,逐渐进入到一种寂静的淡定。水面跳动的不再是雨点,而是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淡字。其中一个淡字被放大,弥漫开来,闯入我的思绪。
淡,与禅不同,是一个离普通人更近的境界。或许禅定为世人所难以企及,但淡定不同,如果你也站在窗前,静静地看雨打水面,一样可以体会到一种淡定的感觉。
所谓天高云淡,而非云无,淡是薄,是寡,是更容易为我辈所能做到的。但使之成为一种常态,则非一朝一夕之功。
淡的境界是什么?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有疏食,有水,有肱可曲而枕之,则乐在其中。这种心态,就是淡的境界。这是一个简单的标准,每一个人面对此境遇,或不堪其忧,或乐在其中,淡或不淡,可立判也。
其实淡不仅是一种境界,还是一种处世的方法。烦恼,困惑,甚或难解的结,一个淡字问题则可迎刃而解。
淡,左水右火,水火相交,此乃六十四卦中既济之象。既济,就是完成,生活中若有此象,则兆示问题的解决。既济卦告诉我们,淡定,可以解决一切难题。
淡定的淡字,还有一个与之通用的澹字。初指水波摇动的样子,后竟与淡通。我们可以理解为波动之后的澹定。这种澹定是经历之后的收获,更为真实和恒定。
淡,澹,如果你不能完全放下,何不先尝试一下看淡它。
良田万顷,日食一升;大厦千间,夜眠八尺。
如果你已有一升之食,八尺之床,其余的还重要吗?
结语:淡,如火烹水,水蒸火尽,让所有的烦恼都随最后一缕青烟飘散。
空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山空乎?江空乎?
非空非非空。据说王勃在写“槛外长江空自流”时,并没有写空字,而是在“长江”和“自流”之间留了白。难道白就是空吗?非空非非空。
《说文》说:“空,窍也。”也就物中之孔,物中没有的那一部分。《老子》说:“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当其无”就是空。因为有空,才有其用。所以真空妙有本是一回事。
真空是什么?非空之空,即为真空。妙有是什么?非有之有,即为妙有。
若想解开空字,就不能回避色字。
色是什么?苏轼的《赤壁赋》云:“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万物本无色,“目遇之而成色”。
我们眼所见的颜色是真实的吗?物体呈现的颜色,其实取决于它对光谱中颜色的吸收。光照在物体上,一部分颜色的光被吸收,未被吸收的颜色被反射出来,于是才有了“目遇之而成色”。如果光谱中所有的颜色都被吸收,那么就是黑,在大空间中,则是一片黑,什么也看不见了。“黑洞”之所以被称作“黑洞”,即缘于此。我们描述某一种物体某一种颜色,并非其真实,在不同光境中,同一物体一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那么哪种颜色才是其本色呢?全颜色或没有颜色才是其本色。所以,空即是色,色即是空。推而广之,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见色不为惧,怕就怕执着于色。如绝字,色旁有丝,丝系于色,则为绝。执着于色,必陷于绝境。
空呢?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执着于空,等同于执着于色。
可见无论空还是色,只有两不执着,才是得其真空妙有。
若有所不空,应当有所空。
不空尚不得,何况得于空。
凡人见不空,亦复见于空。
不见见无见,是实名涅槃。
结语:空,伸出两只拳,你猜哪只手?
舒
舒展,舒畅,舒适,舒带给我们的是打开,是自由的空间,是悠然自得。
《说文》说:“舒,伸也。从舍,从予。”
舍字常用的有两个读音:读上声,是舍弃的舍,即捨的古字。读去声,是馆舍的舍。予字常用的也有两个读音:读上声,是给予的予。读阳平,是代词,指我。
由此舒字可三解。
第一解,舍弃即给予。世间的不如意都来自于过度的贪念。不论是上天的给予还是他人的给予,都需要你有所舍弃。比如你酷爱豪车,但却无房可住,而你的积蓄只够其中的一项花销,为了首先改变无家可归的现状,你只能舍弃所爱。比如面对美食,比如面对感情,比如面对你人生所有的选择,不懂得舍弃,就不会拥有。
孟子有一段经典的话,传诵至今:“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是舍弃与给予的第一义的诠释。
第二解,舍弃自我。若得此境界,则为大舒,即所谓大逍遥。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最根本的是我相,若无我相,自然无人相众生相寿者相。
常有人言舍我其谁。这是我相的大执着甚或执迷。请相信,如果没有你,日月依旧运行,江河依旧奔流。
第三解,客舍我相。我以我的肉身我的意识我的灵魂来此世间,不过是匆匆过客。为一段因缘来去世间,正如《红楼》中所引石湖诗句,无论你是夭是寿,因缘过后,“终须一个土馒头”。
偈曰:
我乃世间客,能舍才是得。
若肯舍我相,所有相皆舍。
佛说法尚应舍,想想看,还有什么不能舍。
结语:舒,砸烂这所房子,让太阳找不到阴影。
识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上说: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受想行识”中的识是什么?这个识就是一切外在反射于内心中的感受。即所谓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以及末那识、阿赖耶识。
那么这些识究竟是否真实呢?我们可以先看看眼识和耳识到底能识些什么。
我们能看到的是一个由七彩构成的世界,赤橙黄绿青蓝紫。每一次面对彩虹,也许我们都会为绚烂的色彩所倾倒,或许还会以为此刻我们饱览了宇宙中的一切色彩。直到一些现代仪器的出现我们才知道,比七彩多得多的色彩其实我们根本无法领略。比紫色光波更短的紫外线,比红色光波更长的红外线,明明布满了我们的眼前,我们却看不见。即使是可见光,面向我们走来的物体发出的光,因为光波压缩,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蓝移;而正在远离我们的物体发出的光,因为光波拉长,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红移。宇宙学家正是根据这一原理,迸发出宇宙大爆炸的灵感。
声音的世界亦复如是。从低频到高频,我们可以听到美妙的音乐。可是宇宙中的声音更多的是低于低频的次声和高于高频的超声。也许大象可以听见,我们却听不见;也许鲨鱼可以听见,我们却听不见。和光波同样的原理,发声物奔向我们,因为压缩了声波,我们的听到的声音就越来越尖锐;发声物离我们远去,因为拉长了声波,我们听到的声音就越来越低沉。比如火车从我们面前呼啸而过,我们就会有此体验。
所以不论是色彩还是声音,眼识耳识都是相,凡所有相,皆非真实。你能相信无数复眼的蜻蜓或者一面一只眼睛的鱼看到的世界和我们看到的世界是一样的吗?那么到底谁眼中的世界是真实的呢?
回头我们再来看看识(識)字的结构。言,音,戈。金文中的識字没有言,只是挂在戈上的音,其实就是最早的旗帜的帜(幟)字。这个幟挂在那里,目的是为了让远处的人能够看到。戈者,兵也;兵者,凶器也。识,就是挂在凶器上的音。放下凶器,你还能听见什么,看见什么?
结语:识,其实是一种蛊惑。捂上耳朵,闭上眼睛,也许可以听见我们灵魂的声音。
为(爲)
《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从此关于“为”还是“无为”,搬弄文字的人你一言我一语,说了两千多年。
那么“为”,到底是什么?
文字学史上有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没见过甲骨文的许慎在《说文》中把“为”字的起源解释为抓耳挠腮的母猴。因此说,和大文字学家许慎相比,我们这一代人实在太幸运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比许慎古老许多的甲骨文。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爲字,除了上面的“爪”字,根本猜不出下面部分到底是什么。是猴子吗?非也。甲骨文很形象地告诉我们,“爪”字下面是一头陆地上最大的动物——象。
大象,为什么被引申到现象、象征的象?根据现有文献,我们还梳理不出清晰的脉络。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推测。
无论是人类出现之前的恐龙,还是当时悠游于远洋中的鲸,都不是先祖所能了解到的。他们能见到的最大的生灵无过于象了,所以他们用象来象征天地万象,以示其大,示其包罗。凡所能眼见,都称之为“象”,而此“象”的意向就等同于后来常用的相貌的“相”。
说到这里,为字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手牵象鼻,是说用手抓住象。在往下理解一层,就是抓住相,即执着于相。
那么“无为”是什么?无为就是不执着于相。因此才无所不为。
《老子》还说:“上德无为而无以为。”
为什么无以为?因为抓住的“相”只是“相”,是被五蕴遮蔽后我们所看到的。本是虚妄,我们如何能抓得住?
大千世界,宇宙万象,在这个我们灵魂客居地方,我们到底能抓住什么?
忽然想起写过的一个小故事,附在文尾:
她说她要气球。
于是我给她买了一只红气球。可是她没抓紧,气球飞走了。于是我又给她买了一只蓝气球。可是她依旧没抓紧,气球飞走了。我第三次给她买了一只黄气球。结果还是眼睁睁看着气球飞走。我索性赤橙黄绿青蓝紫,一口气给她买了七支气球。这一回,她和气球一起飞走了。
她飞走的时候笑得很开心,我听见她在大声喊:抓住了,这一次我真的抓住了!
结语:为,抓住的只能是相。放开手,就可以放飞你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