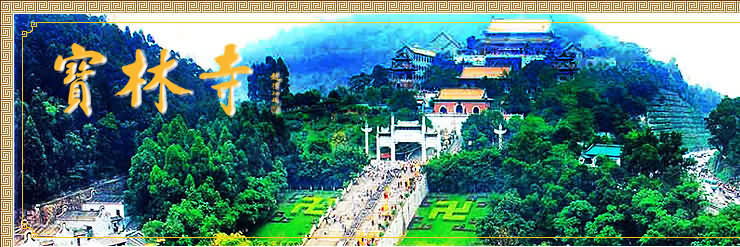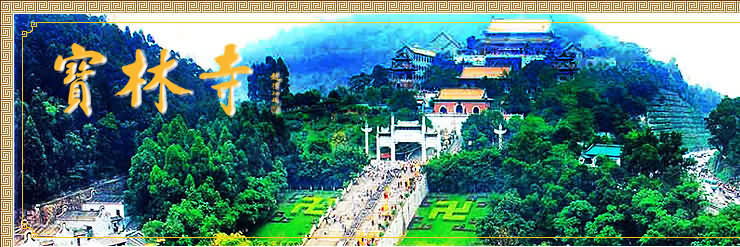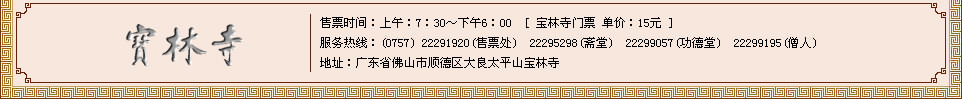戒
文/一苇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佛经上说:“戒是一切善法梯凳。”
古戒字是一个双手捧戈的象形。
不管在什么时候,总有一双手笔直地捧着一柄明晃晃的戈守在你的背后。大大小小的魑魅魍魉因此而望风逃散。
这些魑魅魍魉是什么?贪、嗔、痴,以及由此而生的所有心魔。
这柄戈笔直朝天,杀戮于杀戮之前,因而其实是一种心灵层面的预警。告诉你有所为有所不为;告诉你众善奉行,诸恶莫作。
一个人如果一无所戒,心灵就等同于丢失了所有的免疫系统,难免会被魔鬼所魇,犹如未设防火墙的电脑,无法抵挡病毒的侵袭。
戒是一道门,是走向彼岸之路的第一道门。这一双手是你自己的,这一柄戈也是属于你自己的,但在你跨进这道门槛之前,它们被寄存在大门之内。如果你一生都不肯跨进这扇门,就永远无法享用本属于你自己的心灵守护。
戒的境界或有三种:苦戒、乐戒、不戒而戒。
苦戒是一种对欲望的强行压制。有多少善男信女持戒念佛,虔心修福。对照戒律,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能想什么不能想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甚而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一一奉行不怠。久而久之,成为一种习惯,于是就迈过了这道门槛,苦再不觉为苦。
乐戒是进入大门之后的一种境界。持之以恒的戒行给人带来的不再是痛苦,而是一种超脱的快乐。
不戒而戒,是戒的化境。正如孔子所说:“从心所欲,不逾矩。”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 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水清亦为我所用,水浊亦为我所用。
结语:戒,双手敬持金戈,守护心灵的防火墙。
定
定,一座小房子,一道止步线,一只停住的脚。这就是上下结构的“定”字,字形构成古今几乎没有大的变化。
这只脚是你一直难以停下的匆匆脚步,这道止步线是你心灵的一次呼唤,这座小房子是你心灵的小屋。你一直在匆匆奔走,似乎在寻找什么,可是当你突然听到一声呼唤而停下脚步,才发现你其实就在你心灵的小屋。而你要寻找的东西就在这里。
且看先哲告诉我们些什么。
心住一缘,离于散动,故名定。(大乘义章十三)
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坛经·定慧品)
妄念不生为禅,坐见本性为定。本性者,是汝无心。定者,对境无心,八风不能动。(顿悟入道要门论)
定之境,可谓至简至难。
据说当年苏东坡在瓜州任职,与隔江相望的金山寺佛印禅师颇有来往。苏东坡整日持修佛法,自以为悟得定境,随手写了一首偈语:
稽首天中天,豪光照大千。
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
写罢,暗自得意,差人过江送给佛印禅师。
佛印不发一言,在他的诗偈上连写了两个“放屁”,让来人带回。
苏东坡看了佛印的批语恼羞成怒,亲自过江问罪。
佛印早等在岸边。
苏东坡问他为什么如此蔑视自己的修行。佛印哈哈大笑,回答说:你不是八风吹不动吗,怎么两个屁就把你打过江来了?
可见定境之至难。
定者,或可分为大定与小定。
小定即参禅打坐。烦恼如池中之泥沙,水动则泥沙泛起,水静则泥沙沉淀,所以水浊水清全在水动水静,非干他物。如能坐定,则心之水即可澄净。而搅动池水的正是我们收不住的匆匆脚步。
大定则不定而定,见动不动,无我无境。
结语:定,停下脚步才发现你已经在心灵的小屋,而你苦苦寻找的原来就在你面前。
慧
何谓慧?
初升的红日挂在林间,摇摇摆摆鸣响晨钟。
我看见一个背影孤独地树在寺院的梧桐树下。一把扫帚和人同高,他在扫寺中的落叶。刷,刷……,扫地的声音横插在晨籁的波纹中。
他在扫什么?他是在扫落叶吗?
落叶没了。扫地的人没了。那把大扫帚也没了。
他到底扫掉了什么?
还是让我们回头看看这个慧字吧。
慧,上彗,下心。彗,就是扫帚,与其他扫帚不同的是它是扫除心尘的扫帚。所以所谓慧,就是持一把扫帚守着你的心,“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可是“本来无一物”,你又扫掉了什么呢?
落叶没了。扫地的人没了。那把大扫帚也没了。
我们终于知道了他在扫什么。
如来问:“须菩提,如来有慧眼不?”
须菩提说:“如是,世尊,如来有慧眼。”
那么,我辈可求而得之乎?
《五灯会元》里有一段对话:
“唐宣宗问弘辨禅师曰:云何名戒?对曰:防非止恶谓之戒。帝曰:云何为定?对曰:六根涉境,心不随缘名定。帝曰:云何为慧?对曰:心境俱空,照览无惑名慧。”
可见,戒定慧,就是一条通往慧的坦途。
以戒而定,因定而慧。所谓“非戒无以生定,非定无以生慧”。
六祖在《坛经·定慧品》中说:“定慧犹如何等?犹如灯光。有灯即光,无灯即暗;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名虽有二,体本同一。”
只要你肯把灯点上,自然可以看见光明。
结语:用一把扫帚扫除心上诸尘,你会发现佛门的钥匙就在你掌心。
尊
尊的本意是一种最古老的酒器。
在古人的头脑里,这种酒器甚至与生命的繁育有关。
酒是液体,无以象形,于是古人造字就想起了用盛酒的容器象征酒,这就是“酉”,即最古老的酒字,其实就是画了一个酒尊。
用尊的形象象征酒,那么尊字怎么办?聪明的古人把这个字动态化,在酉字下面加了两只手,这就是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尊字。后来演变成一只手(寸)的今字。用双手将酒捧起,这就是尊,从而一举将名词动词化。
将酒捧起,放到哪里?原来古人是把它放在祭案或祭坛之上。这个尊字所描绘的是一种古老的祭祀。
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最古老的尊,也是最像古“酉”字(如甲骨文)的尊,是大汶口文化的大口尊。一米多高的一个柱状体,很像一个倒置的甲骨文“且”(祖)字,其实就是男性性器的象征。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却只有一个小圜底,根本立不住,可见只有挖一个坑,才能把它植入其中。我们由此隐约目睹了一场宏大的祭祀盛典:祭司们把雄伟的大口尊抬上祭坛,植入坛上的土坑内,然后注入醇酒,象征天公地母之交合,祈求包括庄稼、牲畜和人类自己的所有生命的生生不息与繁盛。
对于古人来说,世间万象均不可思议,而在世间万象中最不可思议的自然是生命,由此人们对生命的崇拜油然而生。
生命只是对人而言吗?非也。我们知道,佛祖可令入无余涅槃的不止是人,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也都在其中。
令人心痛的是,文明从某种角度上说,是一场灾难。自从文明产生以来,直到今天,在人类的世界中,“尊者”为尊,人们为权贵折腰,向金钱低头,忘记了众生平等,忘记了尊重每一个生命。
我曾经困惑,为什么有些远古的部族,会把他们的猎物、食物奉为图腾?后来我渐渐明白,原来这是源于他们已经沉淀在潜意识层中的感恩意识。当其他的生命成为人类的食物,它就是人类生存和物种延续的保障。它们用生命作为对人类的恩典,难道我们不该对它们有感恩之心吗?落红不是无情物,这里面也包括植物,植物也有灵。
众生平等,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感恩的心,去尊重每一个生命。每当你拿起筷子,愿你都能想起那个关于“尊”的古老仪式,怀着对盘中餐的感恩之心,为每一个生命的尊严而祈祷。
结语:尊,是一种态度。它是在感恩土壤中生长起来的虔诚。
僧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却巫山不是云。
如果有一天我们站在心灵的巅峰,俯望五蕴,还有什么可以放不下的呢?
那么有什么力量可以使我们站上心灵的巅峰呢?有一种力量,就是僧。
僧,是什么?左人右曾。是那个告诉我们,人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曾经,都不可得,都是虚妄不真实的那个人。
僧,像一句警言,人所能认知的都已是曾经,也就是说我们所见所闻,都只能是曾经。我们无法拥有所谓的现在,渐行渐远的过去呢,自然更与我们无关。而世间所有的事都无外乎是曾经和即将成为曾经。
也许在我们身边,随遇随成为曾经的感受不易察觉。如果我们把眼睛转向宇宙太空,则可以看得更清楚些。夜晚,当我们仰望太空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被无边的星空所震撼,我们看到众星拱北辰,看到猎户带着他心爱的猎犬追逐天边,好像一切都那么宁静安逸。而其实这一切远非真实,我们所见星系,其距离几乎均以光年计,近则几光年几十光年,远则几万光年几百万光年。我们熟知的牛郎、织女星距离我们也有16光年和26光年之远,由此我们知道,在我们仰望银河的时候,我们见到的至少是牛郎星织女星10几年前20几年前发出的光,而根本不是在我们仰望星空时的光,我们所见早已是曾经。
而尤让我们难以承受的是:不论是什么,一旦成为曾经,将不可改变。面对曾经,我们除了无奈,还能做些什么?
无论你有多么美好的经历还是多么痛苦的经历,都是曾经的往事,一旦成为曾经,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它的虚妄不真实。可是还是有人把希望捆绑在尚未成为曾经的所谓将来,误以为那些才是真实的。其实它们和曾经一样,都是世间这个大幻灯机里的一帧帧图像,所不同的是,曾经在右侧,而这些所谓未发生的在左侧而已。
当我们迷惑其中,不能自拔的时候,我们需要一种力量。于是,僧来到了我们面前。
僧,是梵语僧伽的简称。可以简单概括为聚集在一起奉佛修行的人。他们不仅要修行,还担负着播撒佛法的使命。他就是那个告诉我们人的一切都是曾经的那个人,由此让我们看破所有的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
因此僧被列在佛教三宝之中。如果我们打一个比喻,那么佛法僧三宝中佛是彼岸,法是到达彼岸的船,而僧就是吹动船帆的风。
结语:僧,把一帧帧回忆联缀成风,吹动你投奔彼岸的帆。一切皆是曾经。
俗
俗人昭昭,我独昏昏。
俗人察察,我独闷闷。
————《老子》
俗,拆分为人谷。人之谷,谷之人。是什么谷?是欲望之谷。我们曾说过,谷亦为古欲字,岂不知古欲字或直接写作“俗”,如《毛公鼎》中的欲字即写作俗。《释名•释言语》曰:“俗,欲也。”《荀子•王制》曰:“天下不一,诸侯俗反。”皆其证也。
可见俗欲原本一家。俗是人欲之谷,也是挣扎在欲望谷底的芸芸众生。
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落入谷底?
人从呱呱坠地那一刻起,就开始了这一苦难的历程。所以每一个来到人间的婴儿都用凄厉的啼哭评价这个不得不面对的俗世界。他为什么要哭?因为他对这个欲望的山谷充满了恐惧。此后一生中所有的痛苦,都来自于这个欲望之谷。
深陷在谷底中的我们看见了什么?
我们看到了高不可攀、充满诱惑、形状各异的天。我们把谷口的边缘误作天的形状。由于站在不同的角度,我们看见权势、地位、声誉、财富等等不同的天,诱惑我们像蝼蚁一样奔忙追逐。尽管那些站在谷口外面的哲人用洪亮的声音告诉我们:天,没有形状。可是谷中之人没有一个人会相信。
在欲望之谷底,林林总总的欲望之中最高的欲望又是什么?
爬出谷口!
我们能爬出谷口吗,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爬出谷口吗?
我们都知道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如果我们往坑中注满了水,落入坑中的生命就可以漂浮上来,由此就可以获救。然而坑中的我们人人有漏,注入的水都漏掉了,我们依然无法上岸。所以我们必须弥合我们的漏,而戒定慧也许正是我们堵漏的腻子吧。
面对痛苦中的芸芸众生,我一直在想,这个坑究竟是谁挖的?
忽然有一天,我梦见如来拈花微笑,就在那一刻我才知道世上根本就没有这个坑。
结语:俗,人欲之谷,欲谷之人。谷,本不存在,如果你不再想爬上谷口。
佛
《说文》上说:“佛,见不审也。”就是说看不清,隐隐约约。这个意向我们仍然在用,比如“仿佛”。
自从佛入中土,“佛”忽然间变成了泊在每一个众生身边的船。只可惜我们被五蕴所障,看不清这条船。我们一直在找出路,却不知那条船就在一转身间。我们始终不肯转身,甚至抛下身边这条船,万里迢迢,千辛万苦去灵山寻找佛陀。去求他老人家赐给我们一条船。这一切,只缘于我们看不清。这纷繁的世界,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
“佛”是什么?“佛”也是一种相。不论是这个“佛”字,还是那个菩提树下端坐的悟者,都是一种相。揭开这层相,把“佛”扔掉,即见如来!
如果一下子揭不掉,不如我们先把它分解一下。佛,左人,右弗。弗人也(弗,否定词)。佛的确不是我们血肉之躯的人,禁锢在皮囊中的是人,扔掉皮囊的才是佛。所以说,佛,弗人也。人是一种相,弗人也是一种相,不过是两种状态的标签而已。如果抛开相,那么,所谓弗人,即是人。换言之,所谓佛,即非佛,是名佛。回过头看,因为佛不是人,所以佛就是人。具体地说,佛是觉悟了的人,人是尚未觉悟的佛。“自性若悟,众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众生。”如此而已。
再往下细细剖解,“佛”字右边的“弗”字,原来是一幅修行图。两个竖道从“弓”字中穿过。“弓”就是人因五蕴所迷而见的弯曲的路。而最早的“弗”(如金文)中间的“弓”字,并没有向下的弯曲,也就是说,并不是现在的“弓”字,而是一个自己的“己”字。那么这个“己”为什么是一条弯曲的路?因为我们自己总是被“我相”所障,所以走的路永远是弯路。
看到两条竖道了吗?那就是佛祖指给我们的路,是通往真理的捷径。这条捷径,就是走出自我,超越自我。那么为什么是两条呢?因为佛途绝不止一条,不论入世,不论出世;不论在家,不论出家……
如果我们把拆卸的“佛”再组装起来,发现所谓佛,原来就是超越了自我的人。
自我是什么?自我是造化用皮囊制造出的骗局,所以何必当真。既然是骗局,还有什么值得留恋?扔了吧!“法尚应舍,何况非法。”
结语:佛,走出自我的人。他给我们每个人身边都备下一条走出自我的船。
仁
仁,二人。一人为人,二人为仁。
看看中国的汉字,两个人在一起会是什么情形。
一人在前,一个跟在后,这是“从”字(“從”字的古字就是“从”),人家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两个人同方向靠在一起,这是“比”字。孔子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两个小人在一起嘀嘀咕咕,不知又出什么坏点子。
两个人并排站立,这是“並”字。二力并作一力,所谓“并敌一向,千里杀将”。
一人往左,一人往右,背对着背,这是“北”字,即古“背”字,谁都不理谁,闹别扭,不和你玩了。
两个人一颠一倒,这是“化”字。比如八卦中的阴阳两爻,幻化出无穷世界。
而仁是什么呢?是看不出任何状态的两个人。
儒家对仁的直接或间接释读可谓汗牛充栋。“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只一部《论语》,“仁”字就出现过109次。
但仔细品味,这些解释似乎总差半步。
《广雅》云:“仁,有也。”王念孙解释说:“有,犹友也。”从这里隐约可窥见“仁”之源头。“道生一,一生二。”如果只是单独的一个人,不和任何人产生关系,那么只不过是一个自然的生命而已,什么故事也不会发生。但有了两个人,就产生了关系,就有了利益的趋同和相悖,就有了或和谐一致,或相互矛盾,就有了“从”、“比”、“并”、“北(背)”、“化”,就构成了所谓社会的最基本单元。
所以说:“仁,有也。”这个“有”就是色空之色,有无之有。色、有,是相,是一种自然状态的相。因为自然,所以都是天性使然。
韩非子在解释《老子》时说:“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恶人之有祸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报也。故曰:‘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这种爱是不能自控的、自然流露的。原来仁就是这种发乎内心,发乎天性的“友”(友是什么,古文字告诉我们,友是两只彼此向对方伸出的手)。
仁之爱,是一种原始自然之状态,也是一种博爱之终极境界。
当年佛祖与须菩提两个人在祇园里的一段对话,就在这一对对无数的口耳相传之间,普度了多少众生。千二百五十人“皆大欢喜”,普天之下信众“皆大欢喜”。
结语:仁,是一种相逢,相逢即是缘。若有余力,自度而度人。
信
信,人言为信。这是字形告诉我们的。
可是看看我们的身边,假烟,假酒,假药,假古董,假名牌,在整容横行的当今世界,甚至连一张脸我们都不敢相信是真是假,更何况人言。在一个因蒙尘而异化的世界,人言何足为信?
可是我们的祖先为什么偏偏把信字造作“人言”?
人言即为信,我相信一定是古人的本意。说了,就是一种承诺,既然承诺了,就一定要信守,所谓“言必信”。这是古人的初衷,是古人的理想,也是古人的一种告诫。
因为只有言而有信,我们才能沟通,才能协作,才能达成我们的目标甚而理想。信是一座桥,桥通,我们才能连结起来。
我们每个人都向往心灵的自由,放浪形骸,无所羁绊。可是真正的自由是一种有根的自由,这个根就是信。犹如翱翔于天空的风筝,它的根就是它赖以放飞的线轴。如果线断掉了,它不再有根,它的命运只能是坠落。
信马由缰,是因为我们信任我们的马。
信步,是因为我们信任我们的脚步。
信天游,是因为我们信任我们的梦想。
我们的大自由,靠的什么?靠的是我们的信仰。
如果我们忘记了人言为信,首先应当反省自己:你说过的话,你敢于负责吗?
佛祖说:如来是不打诳语者。
而作为佛的信众呢?我们要做到的是先用信念净化我们的心池,然后把我们想说的话在心池中浸泡了,如此我们的话同样可以成为一种信。
这个世上什么最贵?信。一诺值千金。
结语:信,心灵连结心灵的桥。没有桥的连结,我们将无所固着,四散为漂泊于孤独的浮萍。
困
“困”之为“困”字,曾令我困惑很久。
在一个风清日朗的春日,怀揣着这个陈旧的困惑登上天目湖的游船,在山水之间放飞常年困顿于城市喧嚣的心灵。天高心自远,渐渐感觉到怀中困惑冰释前的松软。
登上最后一站的龙兴岛,沿崎岖的木板山路盘旋而上,路越来越窄,心胸却越来越宽阔。我感觉出打开心结的机遇离我越来越近,果然,猛然间映入眼中的一幕最终打碎了这个郁结多年的困惑,我找到了答案。
我并没有留意这是一棵什么树,它被另一棵树藤紧紧缠绕,好像有几分窒息。这就是我所要寻找的“困”字。
树藤为什么要箍住它?是因为爱,还是因为恨?
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根这样的藤,因为有这根藤,所以箍住对方,箍住自己。解不开,放不下。因此而困,因此而被困。
这棵树是什么,这根藤又是什么?
所有的痛苦都缘于有这棵树,有这根藤。
如果没有这样两粒种子曾经撒落在这里,你能在这里看到什么?什么也看不到。
我们的佛祖生于无忧树下,成道于菩提树下,涅槃于娑罗双树下。为什么佛祖与树如此有缘?佛祖想借此告诉我们什么?
这里真的有一棵树吗?
树是眼所见,藤是心所生。没有树,藤则何以缠绕?没有藤,树则何以被缠绕?况且,其实树本也由心所生。
佛祖问:你看到了什么?答:我看到了一棵树。
佛祖问:你看到了什么?答:哦,我什么也有看到。
在龙兴岛上,我看到一棵树,被藤所困的树。
离开龙兴岛,我什么也没有看到。
结语:困,因为有一棵树,所以树被藤缠住。
归(歸)
传说佛陀有个弟子叫周利盘陀伽,是个愚钝无比的人。无论教他什么,他都学不会。每个人都在嗤笑他,就连佛的弟子们也不愿意与他为伍,没有人相信他会有一天悟道成佛。
既然什么也学不会,佛就给了他一把扫帚,要他打扫庭院,只念一句“扫除尘垢”。 周利盘陀伽就拿着这把佛赋予的扫帚天天打扫,终于有一天他翻越了心中的那座无明之山,豁然开悟。
周利盘陀伽的故事也许就是我们面前这个“歸”字的权威诠释。
歸,有三个部件。阜,一个小土堆、小山丘。止,一只脚,象征行路,象征一个过程。帚,一把扫帚。
歸,手持扫帚,走在山路上,一路走一路扫来。
世间的路就是一个一个崎岖的山丘,扫帚就是我们的信念,走在路上,贵在持之以恒。
那么我们扫除的是什么?我们又归向何处?
我们扫除的是蒙在心镜上的一切尘垢,归依的则是自性三宝。
六祖说: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自心归依觉,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能离财色,名两足尊。自心归依正,念念无邪见,以无邪见故,即无人我贡高贪爱执著,名离欲尊。自心归依净,一切尘劳爱欲境界,自性皆不染著,名众中尊。
佛法僧,觉正净,正是我等归处。
那么我们一路扫来,究竟扫掉了什么?什么也没有扫掉。“世人性本清净,万法从自性生。思量一切恶事,即生恶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
当周利盘陀伽举起扫帚高喊: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他自此悟道。
当你还满眼尘土的时候,你怎么能放下自己的扫帚?当你什么尘土也看不到的时候,你放下的不仅是你的扫帚,而是你的所有。因为你本来什么也没有。
走吧,让我们扛起周利盘陀伽的扫帚,踏上山路,去寻找心灵的彼岸。
结语:归,扛起扫帚,踏上山路,我们回家吧。
息
宠物市场上,经常可以看见一只宠物鼠在风车形状的笼子里不知疲倦地奔跑。可是它无论如何奔跑,始终都在原地。
自以为聪明的人会觉得它十分可笑,岂不知在茫茫红尘中奔忙的我等众生也不过如此。等你有心停下脚步,才会发现,奔跑与不奔跑结果没有什么不同。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么只有停下脚步,你才有可能真正看清面前的一切。
停下,就是息。
息,是休养,是终止抑或开始。
这其中包含了宇宙间最大的辩证法。《易传》中说:“革,水火相息。”革就是旧的消失,新的开始,如水火相灭相生。
虫子消失了,茧蛹就出现了。茧蛹消失了,蝴蝶就出现了。因为灭,所以生。
息,所以静;静,所以入禅定;入禅定,所以达涅槃。
息字,上自下心。自是什么?古字“自”就是人鼻的象形。息的初始意,即为呼吸之运行。以鼻观心,外气自鼻入心,心气上达于鼻,人与宇宙就这样联系在一起。
为什么以鼻子指代自我?因为自我本不存在。我是什么?身体的哪一部分是“我”?是头,是躯干,是五脏六腑?都是,都不是。那就用面部的中央说事吧。于是,鼻子就成了我。
以我之象征的鼻子吸气下入于心,然后由心回到鼻子,回到自我。心神凝聚于呼吸间,让四肢消失,让躯体消失,只有呼吸在流动,最后连呼吸也不再存在,宇宙融在我中,我融在宇宙中……
于是我们把心放下,自我也随之落地。息也不存在了。
一切诸法中,因缘空无主。
息心达本源,故号为沙门。
结语:息,把你指向鼻子的手放下,把心放下,当你真地找不到自我的时候,却找到了自性。
梵
朝梵林未曙,夜禅山更寂。
这片森林是谁种的?
我们为什么来到这片森林?
我们是怎样来到这片森林?
我们为什么迷失在这片森林?
迷失在森林中,我们该怎么办?
这么多人在一起,却看不到彼此,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森林中独行。时而看起来无路可走,时而看起来路有千条,却又难以选择。
荆棘拦住去路,枝叶遮住视线,每个寻求摆脱的人,都注定是一次苦旅。如果肯歇住脚,看看身边的树在做什么,也许就会明白,你该做什么。
这片森林是我们自己种的。
我们为自己的苦果来到这里。
我们是被自己送到这里来的。
我们是因为欲望迷失在森林。
迷失在森林中,最好的办法是收住自己的脚步,作一棵森林中的树,作一棵森林中最平凡的树。
那么平凡究竟是什么?
有一天,庄子来到一座山,看见有人在伐木,奇怪的是,面前有一棵参天大树他却视而不见。庄子问他为什么,他解释说,这是一棵不成材的树。庄子下山的时候,这里的朋友请他吃饭,让下人杀一只鹅。下人问他的主人,一只会叫的,一只不会叫的,杀哪一只。主人说,当然杀那只不会叫的。
庄子的弟子很困惑,问他的老师:山上的树因为不成材得以保命,而这只鹅却为它的不材而丧命。到底是应该选择成材还是不成材?
庄子说:如果让我选,自然是在成材与不成材之间。
这或许就是对平凡的注解。这个平凡是一种大境界,是自由游走于材与不材之间的大境界。
结语:梵,如果你迷失在林中,不如就作一棵林中平凡的小树。
悲
悲者有二,即自悲、悲他。悲伤之悲为自悲,悲悯之悲为悲他。
自悲之悲,心非也。心为五蕴遮蔽,以相为真,心上承受着沉重的是是非非。悲,是一种苦难。
当年庄子的妻子病故。朋友惠子去看他,居然见他蹲在那里敲着瓦盆唱歌。惠子很气愤,质问他:妻子和你朝夕相处这么多年,如今撒手而去,你不哭也就罢了,还在这里敲着瓦盆唱歌,是不是太过分了。
庄子说:恩,我开始的时候,和你的想法一样,也难免心中悲伤。可是后来我想通了。你想,一个人的生命从哪里来?从无中来。开始若有若无,继而有了形体,形体中赋予了生命。现在人故去了,生命消失,而后形体消失。这不和春夏秋冬一样吗?看人之生死,同四季更迭一样,不知道我还要哭什么。
这就是对自悲的抛弃,悲伤的缘由本不存在,哪里来的悲伤。
悲他之悲,非心也。以悲悯之怀救拔众生,而众生所惑,皆缘于种种相,拨除诸相,即见本心。而本心何在?本心无所在,无所不在。所谓心者,即非心,是名心也。悲,是一种苦难的救拔。
放下自我的悲伤,就可以打开悲悯之怀。
此悲又有二,所谓小悲和大悲。
小悲者,一箪食,一壶浆。雨中送伞,雪里送炭。有时候不过是身边举手之劳,只看有心无心而已。一点小事,度他而自度。
大悲者,乃修无量之福德。救人莫若救心,若能教人心向善,人心向佛,度人于苦海,方为大悲,如我慈悲菩萨。即我佛所云,即使以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不若“于此经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为他人说”。
结语:悲,把心上的是是非非放下,让悲伤的蛹破茧为悲悯的蝴蝶。
贪
在贪嗔痴三毒中,贪是第一毒,它是这个世上的万恶之根,万苦之源。
与贪伴生的是痛苦,是悔恨,是罪恶。
自从降临这个世界,贪婪就和我们一起成长,从贪吃、贪玩,到贪财、贪色、贪名、贪权……
世上有百贪万贪,像一串又一串的诱饵,唆使我们走向一个又一个痛苦和罪恶的深渊。
最可怕的是一个个贪婪汇总起来的人类的贪婪,正在一步步毁掉我们的大地,毁掉我们的蓝天,毁掉地球生命的未来。殊不知,我们的所谓现代文明正是架构在贪婪的肩膀上。
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代人类发明了一个解剖贪婪的标准模型——股市。人们因为贪婪像疯子一样闯进这里,然后在贪婪的驱使下一次次操作,一次次悔恨,一次次痛苦。套牢痛苦,割肉痛苦,卖早了痛苦,卖晚了痛苦,赔多了痛苦,挣少了痛苦。如果世上真的有什么后悔药,拿到这里卖,一瞬间就会被哄抢一空。人类的贪婪在这里被描摹的极其生动。
可怜的我辈众生。
回头看看这个贪字到底是什么。
今,贝。今是现在,是当下;贝,被古人用作代指财富。贪,是眼前看见的财。也许转过脸,就不知何处去了。我辈众生却为此而倾其一生之精力,苦苦追逐。
贪财,花掉的不见了,堆在那里的与你何干?贪色,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终究是一副肉皮囊。贪名,百年之后,人已成灰,名何附焉?贪权,在位,人畏之,去位,人弃之……
还记得《红楼梦》中的《好了歌》吗?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 ……
结语:贪,是魔鬼扔在你眼前的诱饵,其实你只须抬抬头,就可以看见魔鬼的利爪。
艮
艮,对于现代人来说,似乎渐渐有几分陌生,有几分距离感。如果不是给它穿靴戴帽装扮起来(如良、根、退),甚至想不起它念什么。
那么艮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离我们距离越来越远?
艮的最好注脚无疑是《周易》中的八卦卦象。
艮,是八卦中的一卦。《周易》中艮卦的卦辞留给我们无限的遐想:“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多么空灵高远的一种境界。
艮字的本义,历史上有很多解释,我喜欢高亨先生的说法,艮字从目从匕,而甲骨文、金文的匕是“人”字的反写,那么艮其实就是见(見)的反写,是回头往回看,是顾,是注视。这里就出现了两个要点,一个是回头,一个是注视,而不论是回头,还是注视,都需要先停下来,说的文雅一点,就是止而观。
艮卦的意象是山。山是最大的止,最大的静,最大的注视。我们常说心如止水,但止水如遇风则不再是止水,而不论山风如何吹,山却可以屹然不动。艮卦的卦象为一阳在外在上,二阴在内在下,阳为动为实,阴为静为虚。山为实相,而至静致虚。这就是老子说的“致虚极,守静笃”,这就是艮背行庭不见其人的空灵境界。
纷繁尘世,多需要我们停下自己的脚步,回头看看我们走过的路,静下心来想想我们究竟在做什么。你真的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吗?不妨来读解一下这个远离我们已经很久的艮字吧。
艮是山,是停下,是回头,是注视,是凝想,是一种入定,是一种修为。所以周敦颐说:一部《法华经》,只消一个艮字可了。
刚才我们说过穿靴戴帽,其实再读一读那么穿了靴戴了帽的艮字,也许会帮助我们走得更深远一些。比如“恳”字。尽管想到六书体系的惨遭蹂躏,我们会抱怨简化字带来的危害,但不得不承认,有时候简化字也会给我们带来灵感,恳字就是一例。恳字本写为懇,如今简化为恳。上艮下心,艮为山,如果你已经坐定为一座山,你的心自然就会放到山下。《一切经音义》引《通俗文》说:至诚曰恳。诚是什么,诚就是非骗局,就是本原。当你静坐为山,放下你的心,就自然会找到你的本原。
结语:艮,停下来,回过头,如果你已经是一座山,还需要寻找归宿吗?
兑
《五灯会元·释迦牟尼佛》上有一段文字:“世尊于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
这是一个流传了2500多年的秘密,这是一个永恒而又美妙的瞬间,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微笑。
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在参悟这个神秘的微笑。可惜我们为众相所迷,需要一个形象,作为一扇门,作为一条路的起点。
于是“兑”字走进了我们的视线。
兑是一个古老的文字,也是《周易》中的八卦之一。在历代的解字当中,林义光的说法最为贴切,他在《文源》中的解释是:“从人、口、八。八,分也。人笑故口分开。”甲骨文之“兑”字也验证了他的说法,一个人张开的嘴上是一个代表着分开的“八”字,的确是一个微笑着的人。
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个“兑”字,是否也看出了一个安详的微笑?而这个微笑着的人是否就是那个灵山会上的摩诃迦叶?也许看到这里,你也会有一个会心的微笑。
八卦中的兑卦,初爻二爻为阳,三爻为阴。初为长,二为中,三为少。所以兑卦的意向之一为少女,兑也是少女的微笑。清纯无邪,一尘不染,这也许正是迦叶之笑的起点。
兑卦《彖传》的解释是:“兑,说也。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文》采用的正是《彖传》的解释,即:“兑,说也。”说,是古“悦”字(上古无“悦”字),也就是愉悦的意思。其实不也是微笑吗?
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个“说”,在今天的使用上,是佛所说的“不可说”的“说”,原来这一笑是不可说的,所谓“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是也。
“兑”,可以仰望,也可以让它走下神坛,来到我们身边。所以 “兑”可以分为三种境界:生活中的微笑,少女的微笑,迦叶的微笑。
迦叶之微笑,是我们终生之憧憬,或不可企及。少女之微笑,因为它的可贵,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怜惜。生活中的微笑,我们为什么不去好好品味?
如果有一颗善良的心,感恩的心,阳光的心,生活中我们的眼中也许就看不到坎坷,看不到不公,看不到阴影。
不论你遇到什么,你微笑了吗?
结语:兑,你看他笑他就笑。今天你微笑了吗?
坎
坎,土欠也,土欠即是坑。这是坎之本义。世人所谓坎坷,即此义。
魏源《无量寿经会译叙》中说:“娑婆世界,本华藏世界第十三重,众生视为坑坎土石者。世尊以神足蹑之,立地皆为琉璃宝地。”
娑婆世界,芸芸众生,无人不叹人生之坎坷。为何佛立处,立为琉璃宝地?原来非地坎坷,而是心坎坷。
何谓坎坷?所愿之事不如愿,即被视为坎坷。如无所愿,何来不如愿?即有所愿,尽力而为之,其余则顺其自然,如愿不如愿,皆坦然受之,同样感受不到坎坷何在。岂不脚下亦尽是琉璃宝地。 “无平不陂”,无平则无陂,无陂则无平,如果心无坦途之望,脚下自然亦无坎坷之困。不怕路之坎,只怕心之坎。
如上所言,土坑为坎,故能陷人,于是被视为险。如果你不是行人,而是这个土坑,则完全是另外一种境况。土坑因为在下,因为虚空,所以可以容物。坎若为我等虚怀,荣辱悲喜,还有什么不可以容纳。
回头我们再看看八卦中的坎。坎为坑为沟,在下位,则常为流水所居。故《周易》以坎象水。坎之卦象两阴夹一阳,如果把卦象立起来,然后让它流动弯曲起来,就是一个标准的古“水”字。
《老子》中有两段关于水的文字: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
水之至善如此,可惜“天下莫不知”,却“莫能行”。如果知之且行之,则人人可几于道。
结语:坎,是坑,是水。如果你把它放在路上,它会挡住你的脚步;如果你把它变成你的胸怀,你的面前将是一片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