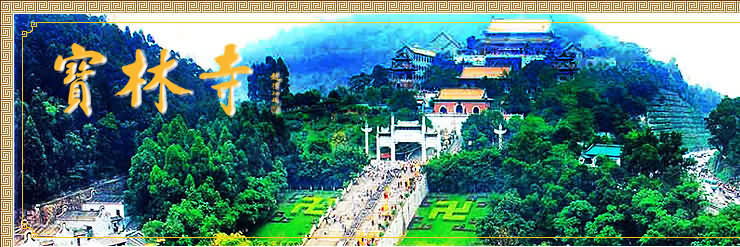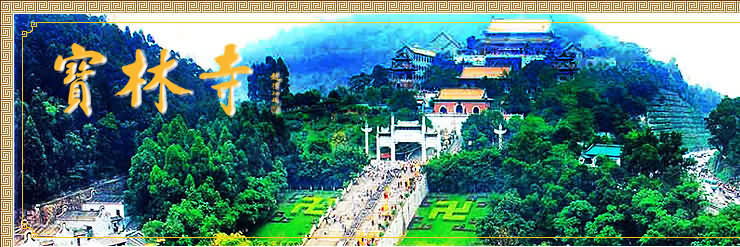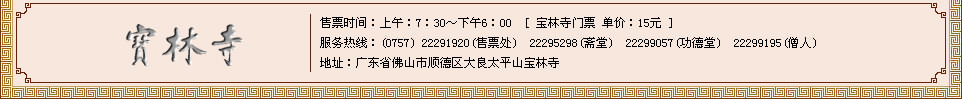名
文/一苇
人的一生最容易为什么所累?为名为累。
那么名到底是什么?回头来剖析这个汉字,或许会有所收获。
名,由一个夕字和一个口字组成,从甲骨文到汉简,如何排列并不固定,但这两个元素始终如一。
如此,意向很明确,就是晚上互相看不见的时候,用口喊出来以示分别。通俗点说,比如夜深人静看见院子里有人,你会问:谁?对方自报名字。这就是名的由来。有《说文》为证:“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可见,名的出现是为了区别不同的人不同的事物,人的思维只有依靠这种区别才可以运转,所以它其实是人逻辑判断和逻辑思维的工具而已,并非一种真实存在。庄子说:“名者,实之宾也。”而所谓实,其实就是相,名呢,又是相的标签而已。如果当年把人呼作马,把花呼作虫,沿袭下来,我们今天就会很自然地把人间称为马间,把风花雪月称为风虫雪月了。佛说凡所有相都是虚妄,相的标签则更是一种虚妄。
由名的本义发展出来的两个主要意向,一是针对人的,是名声、名誉的名;一是针对万事万物的,可以理解为语言文字,是用于解释说明所有一切的名。二者都是一种标签,都是一种虚妄。
《老子》开篇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此名即是可以解释可以言传之意,所以说,如果名可名,佛和迦叶当年在灵山,也不需要演出一场拈花微笑了。佛说:“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佛说:“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佛还在不断地使用独有的三段论:“佛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随破随立,随立随破,就是生怕听者执着于此名相。
而古往今来多少人为此追逐一生的名声、名誉之名更是一种虚妄。你的名字,只不过是一种互相区别的工具而已,它能标识的只能是你的一副皮囊,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连皮囊都带不走,还能带走贴在皮囊上的标签吗?历史上有多少人功成名就,“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是留下的名到底和那个已经化为尘土的人有又什么关系呢?况且几万年下去几亿年下去,连这个空名也终究要化为乌有。当年,陶渊明已不愿“以心为形役”,更不要说作为形之标签的名了。
我喜欢柳三变的那种洒脱,“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结语:名,就是贴在这身皮囊上的标签。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连皮囊都带不走,名又与你何干?
法
两千多年前,有一位智者来到河边,站在那里看滔滔奔流的河水。
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季节,是哪条河,智者是独自一人还是弟子成群。
他说:逝者如斯夫!
于是这个声音回响了两千年。
又过了一千多年,有一位智者来到江边。
季节是秋天,一个月朗风清之夜,智者与友人泛舟于赤壁。
他说: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
又过了一千多年,有一位愚者来到了生命的河边,寻找两千多年前的那条河和一千多年前的那条江。
他什么也没有找到,临走的时候蓦然回首,却捡到了一个字,这个字就是:法。
法,左边是水,右边是去,原来是:水去也。这不就是“逝者如斯夫”吗?还有什么不像这滔滔的河水奔腾而去?
细说起来,这个法字其实是古时候的一个简化字,最初的法字字形中还含有一个叫做廌的神秘动物,可是自从这个神秘的动物走了以后,这个法字的禅意于是就浮出了水面。世间最根本的大法是什么,难道不正是这不断逝去的滔滔河水吗?
逝者如斯夫!这个声音太响亮,所以听者的思路可以跟着它在宇宙间无限穿越,一直等到一千年后,我们才听到了它的回声:未尝往也!
这奔流不息的河水真地在流逝吗?你能找到两千年前那条河吗?你能找到一千年前那条江吗?你能找到昨天刚刚经过的那条小溪吗?无所从来,何以有所去?
就连这天地间的根本大法其实也未尝来亦未尝往,所以佛说如来无法可说,佛说法其实也是个比喻。就连这个法都是最终要舍弃的,更何况非法?
可笑那位智者在泛舟赤壁发出千年慨叹之后,一千多年间,多少墨客为了那个赤壁是真是假而聚讼不休,大叫此赤壁非彼赤壁也。
此赤壁在哪里,彼赤壁又在哪里?
结语:法,水去也。滔滔河水奔逝而去,此乃天地间之大法。河水真地去了吗?
禅
禅,是梵语“禅那”的简称。可是这个禅字一入中土,似乎就经历一场涅槃,浴火重生,脱胎为一个新的生命。
凡事都有机缘,这个禅字不被译为缠,亦不被译为阐,自然有它的宿命。禅字左边的“示”,远古时是一个几案或高台的象形,只有被崇拜被敬仰的才会被供在案上接受顶礼膜拜,所有以示做偏旁的字往往表示一种虔诚和敬畏。而右边的“单”,就是孤单,一个人,独自的意思。独自一个人而有所敬畏,这不就是先贤经常挂在嘴边的“慎独”吗?其中的巧合恰恰是一种宿命。
所谓慎独,大致可以有三种境界。
一种是独处而依然有所敬畏。《中庸》上说:“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即使无人在旁,一个人依然能约束自己,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如此慎独已难以企及,尤其是在物欲横流、无所忌惮的现实世界,这两个字恐怕只能被当作书法挂在墙上。即使如此,此慎独还在禅的门外。
第二种境界就是禅定,远离红尘,独自一人参禅打坐,让内心世界的波澜归于宁静,泥沙沉淀,还一池澄澈。天淡云远,山幽林静,在心灵的尽处,忽然照见五蕴皆空。
第三种境界是不慎而慎,无独而独。这就是《庄子》所说能“外天下”“外物”“外生”的“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这种“独”乃大道也。如此慎独,不必在深山古寺,不必离群索居,见无所见,闻无所闻,连灵魂都不知在何处,还需要净化些什么?这是慎独的至高境界,也是禅的精髓。
大哉禅兮,无处可见却无处不在!
结语:禅,慎独的一种至高境界。因为走入孤独灵魂的深处而打开了孤独的灵
化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
《庄子》开篇即以鲲化为鹏始,洋洋洒洒,徜徉于“化”间,直到庄周梦化为蝴蝶,蝴蝶梦化为庄周,化渐入化境。
化,追溯至甲骨文,乃二人形,只不过这两个人一个人正立,一人倒立。切莫以为这是一颠一倒的两个人,其实这是一个人一正一反亦即一阴一阳的两种状态。恰似太极图中的阴阳鱼,一种状态总在不断地走向它的反面。这就是化字的由来。更不要以为只有人在一正一反一阴一阳不断走向自己的反面,“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以人形为字,只为就近取譬而已。
《庄子》里还有一个小故事:说子来有病,眼见着快死了。他的朋友子犁来看他,见他的妻儿围着他哭,便大声喝斥说:“躲开!别惊动他的化!”随后又感慨说:“伟哉造化!又要把你变成什么呢?是要把你变成老鼠的肝,还是要把你变成虫子的腿?”
听起来十分荒唐,细想一下却绝非胡言。一个人生命终结,腐烂在土里,或被细菌分解,或被虫豸噬咬,或被植物吸收,均可化为另一种生命。所不同的是自我意识的转化而已。此亦所谓“无不毁也,无不成也”。所以即使单从生命的角度,亦无所谓生,亦无所谓死,所谓生死,只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转换。
打开道家门来看:化者,“二”也,阴阳之“二”也,生三生万物之“二”也。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打开儒家门来看:仁为“二人”,化亦为“二人”。静者为仁,动者为化。
打开佛家门来看:一念不生,归于佛性。“思量恶事,化为地狱;思量善事,化为天堂;毒害化为龙蛇,慈悲化为菩萨;智慧化为上界,愚痴化为下方。”此所谓千百亿化身。
世间万象皆为造化所化,并非真实所在。只因眼耳鼻舌身意所受,而成万象。如能照见五蕴皆空,则万化归一。
结语:化,犹如一部投影机,把造物主不断变幻的想象映在天地间的幕布上。
德
德的古字一边为路形,一边为上直下心。
路象征人生之路,包括人世间,包括心灵;直的象形很有意思,是一只眼睛投出的直线,有时候会在这条直线上加一个点,从眼睛中看过去,如果有一个点挡在眼前,挡住的自然是这条直线的延伸,所谓直与不直,可见取决于眼睛所见;下面的心是一个心脏的象形,而象征的则是心灵。
由此可见,德的造字意向是以直心而行于路。也就是品德、德行的“德”。而功德、恩德之“德”的引申义又从何而来呢?
如果一个人能真正做到直心而行于路,也就是怀揣直心而有所行,自然会有所收获,也就是世俗之人所见之利。因此,《广雅》上说:“德,得也。”这就是恩德、功德的“德”。
拆析“德”字,其中的第一要素就是直,而德与直又有本质之不同。德的直是心灵层面的,是有所行的,从而有所获。所以孔子在纠正“以德报怨”的说法时说:“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正因为此“直”有路有心,所以说“德”是可以修来的。比如反躬自省,比如与人为善,均可以修来功德。而在诸功德中,最大的功德又是什么呢?《金刚经》中说:“以要言之,是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如来为发大乘者说,为发最上乘者说。若有人能受持读诵,广为人说,如来悉知是人、悉见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可见广布佛法才是世间第一功德。
所谓德是直心修为而“德”,而非求德而“德”,所以德的最高境界是老子所说的“上德不德”,这是德的精髓所在。为求德而修德,所得之德,充其量为“下德”。
德是人生在世安身立命的第一准则。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可见在道德仁义礼中,德在自然之道之后,而在仁义礼之前。德,其实就是自然之道在人性中的一种体现。
结语:德,直心而行,自然有所得,而实无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