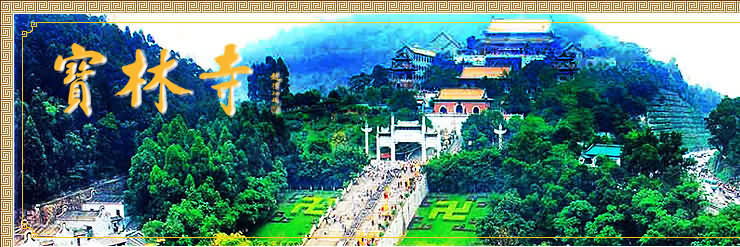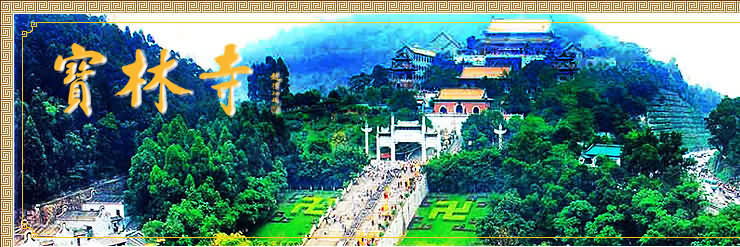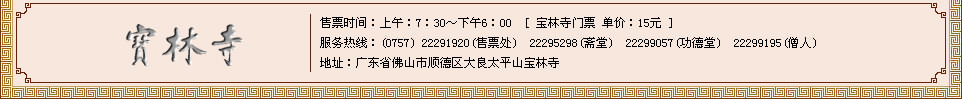齐(齊)
文/一苇
齐(齊)字演化成如今的样子,已经没有了造字之初的旨趣。
最初的古字是三支高矮不齐的箭头(甲骨文、金文)。用三支高矮不齐的箭头来会意“齐”字,不能不让我们这些后辈为古人的精妙构思拍案惊奇。
齐犹不齐。世上不可能存在一个绝对的齐,比如我们分明看两个跑百米的选手同时撞线,但如果把时间精确到百分之一秒甚或千分之一秒,即可分出前后。
放到众生中间命运更是各有不齐。有的生命托生为人,有的生命托生为蝼蚁。有的妻妾成群,儿孙满堂;有的形单影只,孤苦一生。有的人富贵,有的人贫贱;有的人长寿,有的人早夭;有的人成就大业,有的人庸庸碌碌。没有哪两个人的命运会是等齐的。
然而借用佛的一种表述方式:所谓齐,即非齐,是名齐。
虽然三支箭头高低不齐,但却是三箭齐发,都在飞行途中,且错落有致。这就是一种秩序,一种化于自然的秩序。从视觉上看,唯有这种错落有致才是一种平衡的美、齐的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齐家就是理顺源于自然的秩序。
齐,是一根轴心线。
如果你在此刻多得了,那么要么你从前有所失,要么将来有所失。如果你在此处多得了,那么你在彼处就会有所失。有的人有旷世奇才,却早早夭折;有的人腰缠万贯,却丧失了亲情。这一切,都是因为这根轴心线。所以好运当头的时候且莫得意,恶运降临的时候且莫悲哀。推而广之,前生来世,也在这一法则之内。不如此,则无以言平衡和谐,则无以言齐。
除此之外,还有更大的齐。比如生命的平等,用针扎穷人是疼,用针扎富人也是疼。死亡面前更是平等,一个皇帝和一个乞丐,生命的结局是一样的。不会因为你是皇帝就可以万岁万岁万万岁。
齐,最终告诉你一个秘密:如果你有缺陷,那么你应为此感到欣慰。如果你很平庸,那么或许你比别人更安全。
结语:齐,是上帝想象的一根轴心线,波峰浪谷总归于平。
人
最初的“人”字是一个侧向曲背人形的简笔画。隶化以后变成如今的模样。看似一个将笔画拉直的简单过程,细一想,也是一个由形象走向意象的过程。
因为这个“人”字,已经由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且相互支撑,这时候的人缺一边另一边也就无法独存。这就是佛祖所说的我相、人相的“人”。人是典型的社会动物,一个人无法独立生存,两个人则大矣。
两个人就可以阴阳合卺,就可以演绎亚当夏娃的故事,就可以衍化生生不息的人类社会。八卦的无限变化正来自于最简单的阴阳两爻。
两个人可以架起一个房顶,这个“人”从一个侧向的人变成一个侧向的歇山式房顶,这就是家,是一个可以遮风避雨,享受温馨的地方。
我们还可以把它意会为两条腿站立起来的人。因为一场灾难,大森林变成了草原,我们和猿兄弟道了别,从树上下了地,并硬是依靠两条腿站了起来。这一站就从此走上摆脱蛮荒苦苦追逐文明的路,并一发而不可收。
此后的人类继续经历着一场又一场的灾难,而这些灾难已经不仅仅是老天的示惩,更多的是我们人类自己的杰作。倾轧、抢夺、屠杀,人类因为迷惑于我相人相而拼命地制造着各种各样的痛苦。
心静的时候我们会坐在石头上遐想:
为什么最为复杂的人,笔画最简单?
古人不知道进化论,为什么能让这个“人”字两条腿站起来?
站起来的“人”究竟是福是祸?
造化制造了人,为什么同时制造了“人相”来阻挡人的心路,让人执着于我相人相而迷失了真我?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可叹这么多为什么也是一种着相呀!
结语:人,因为站起来,所以走出蛮荒,走入围城。
回
回的古义是旋涡。甲骨文、金文和说文古文都是画了一个简笔的旋涡。往前追溯,大西北马家窑文化的遗址中就出土过画着旋涡纹的彩陶,类似的彩陶纹在时代大约相近的渤海两岸也有发现。这可能就是最早的“回”字了。
这个简单的“回”字蕴涵了古人的无穷智慧。回就是旋转,就是从起点到终点,也许是简单重复,也许是螺旋式上升,从而演示了宇宙甚至生命世界的终极规律。
地球自身在转,月亮围绕地球转,地球携月亮围绕太阳转,太阳携太阳系的所有成员围绕银河系的中心转,毫无疑问,银河系也在围绕着一个中心点转,从现代人的认知度出发,这个中心点可能就是宇宙的轴心了。
生命也是一样,总是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不会偏离这个轮回的轨迹。甚至人的感觉也是如此。据说人在一个没有参照物的地方沿着一条自认为的直线行走,比如在浩瀚无边的沙漠里,总是会又转回到起点。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识这个“回”字。所以有位禅师说:
荆棘丛中下脚易,
月明帘下转身难。
宇宙的一切都在回转之中,唯有人心最难回转。有人一生奔波,从不肯回头。有人则有为一个信念或一个欲望一直向前,从不回头。
甚至学佛参禅的人为寻找心灵的彼岸,独自划一条小舟在苦海中航行,也总是盯着前头的光景。殊不知只要一回头,彼岸就在眼前。
最让人心痛的是当一个人面临绝路的时候,还要继续往前走,死不回头。
回头如此之难,究竟是为什么?
结语:回是旋转,是归。前路漫漫,回头才是岸。
道
我们每天都在说:知道了。
因为就这样至少说了几百年,所以我们从来没有为这句话感到不安。
可是坐下来仔细玩味一下,却不禁惊出一身冷汗。
知道了。了不得,这话说的太大,道是随随便便可以知的吗?说了几百的大话而不自知,还敢说知道,真可谓妄自尊大。
什么是道?
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故强字之曰道。”这个独立于万物之外又无处不在的东西逼着老子给它强起了个名字。他又说:“道可道,非常道。”连他老人家都说不清,我们还敢妄称“知道”,想起来真是惭愧。
道,由首和走之组成,古字中(如金文)往往是“首”字夹在“行”中,“行”就是路的意思,这两种构成,都是首在行走,也就是头脑在行走。有的时候加一只手,隶定以后为“寸”字,组合起来即是“導”(导),道和导在古时本来就是一个字。
头脑在行走,谁的头脑在行走,在哪里行走?看不见,摸不着,所以古人说“大道无形”,“形而上者谓之道”。这个头脑如果是天的,那么这个道就是天的法则,自然的法则,包括可知的不可知的;如果是人的,那么这个道就是人的法则,某个人群的甚而社会的法则,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那么这个法则在哪里行走?天之道不在日月星辰间行走,也不在山河大地间行走,但它左右着日月星辰,左右着山河大地;人之道不在人的行为意识中行走,也不在人的历史中行走,但它左右着人的行为意识,左右着人的历史。
为剖明一个道字,古人可谓呕心沥血。儒释道三教多少先贤都曾苦苦求索过,当他们豁然觉悟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们什么呢?儒家先贤说:“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佛说:“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老子的《道德经》中的《道经》通篇都在探究道是什么,结论还是“道可道,非常道。”那么道究竟是什么,我终于有一点明白,也许大概可能,老实说,我不知道。
结语:道,头脑在行走。那么究竟什么是道,老实说,我不知道。
有
古字最早的“有”是只手,如甲骨文,后来这只空着的手提上了一块肉,如金文,这也就成为现在的“有”字。上面是一只手,不过横撇已经拉直,下面是个月,这个月其实就是肉,“有”的意思就是手持肉。汉字中多数“月”字本是“肉”字的简写,如脸、肤、腹等等,都是肉字旁,千万别把它当成月字旁,这些字和月亮没有关系。
一个有字,从一只空手,到手持一块肉,谁成想一下子所有的烦恼都从这块肉中喷涌而出,演绎出大千世界一幕幕炎凉悲欢。
其实最可怕的手并不是我们的肉手,而是从心中生出的手,而这只心中的手提着的最大一块肉就是我们各自沉重的肉身。
自从手中拿了这块肉,我们就有了“有”,因为有了“有”,我们就开始害怕失去。而不管如何患得患失,你所拥有的一切终究要失去。因为一个人最大的“有”就是生命,而生命也总有一天会离我们而去。
我们通常把生命的有无定义为生与死,生命的有是生,生命的无是死,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活着的人其实都曾经死过,因为我们的生命都是从无中来。那么死是什么?生又是什么?佛经上说:“一切无涅槃,无有涅槃佛,无有佛涅槃,远离觉所觉,若有若无有,是二悉俱离。”死就是生命的一种无的状态,生就是生命的一种有的状态,所谓状态就是一种表象,就是佛所说的相。不论是生还是死,都是一种相。那么生之前是死,死之前是什么?生之后是死,死之后又是什么?其实这些都不重要,因为它不论是什么,都不外乎是一种相而已。
既然如此,这种“有”又“于我何有哉”?
《五灯会元》里有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故事,有人来看望佛,不好空着手,于是捧来了鲜花。佛说,放下吧。于是他把左手的花放下。佛又说,放下吧。于是他把右手的花放下。佛还是说,放下吧。他一时茫然,摊开手说,没了。其实佛让他放下的是他心里的手拿着的那个肉身,也就是放下这个最难放下的“有”。
我们的祖先和我佛几乎有同样的感悟,所以他们造字之初“有”字是一只空着的手,后来我们这只空着的手拿了肉,于是也就拿来了这种种的烦恼。《说文》上解释“有”字时说, “有,不宜有也。”就是说,“有”的意思就是本不该有结果却有了。既然本不该有,为什么还不放下?
结语:有,就是手里拿着。放下吧,放下即可皈依。
得
我们每天都在为一个“得”字奔忙。金钱,权位,学历,感情,林林总总。
“得”,是什么?回头拆解一下最早的古字,左边是一个剖成一半的十字路口,右边上面是一只贝,下面是一只拿着贝的手。得,就是在路上拾到一只贝。
从字面上看,或许有两种解释:一是从路上偶然捡到的,有好运躲都躲不过。一是经过千难万险,一路上苦苦追寻,终于获取的。其实两者的终极意义并没有区别,都是把不是你的变成是你的。
可是不论是哪一种对你充满诱惑的东西,只要你得到了,你最怕的是什么?自然是失去。《说文》段注说:“在手而逸去为失。”
既然在手上却又跑了是“失”,而我们所畏惧的正是这个“失”,那么如果不在手呢?不在手,自然就无所失。
人生不满百,人在世上走这一遭,是真真切切的路过。每个人都是从生之前的来处来,到死之后的去处去,中间这一段如此短暂的生命状态,其实是这个过程中细不容发的间隙,况且这个过程本不成其过程。而在路过的时候捡到的所有东西,在你离开的时候都带不走,所以除了那个如如不动的本心,其余的都不是你的。所有得都是相,都是虚妄。“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记得佛说:“如来在燃灯佛所,于法实无所得。”连佛于法都无所得,凡尘能有何所得?
可怜我辈凡俗,“得之若惊,失之若惊”,被一个得字搅得终生难得安宁。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所以孔夫子曾告诫我们,尤其是年老的人,“戒之在得”。
尘世间有一个非常可笑的口号,叫做“志在必得”。其实如果你能坐下来,平心静气地梳理,你会发现你曾经得到的,都在一件件地失去。比如青春,比如所谓的一段辉煌。那些曾在某个职位上享受过一呼百喏的权威的人,退下来的时候最难适应这种得而复失的感觉。而没有得到过这种威权的人,就毋须体味这种失落。即使有些看起来好像终生相伴的东西,在你的肉体消失以后也不为你所有了。连肉体归根结底都不是你的,你还能得到什么?
既然如此,你还要“志在必得”些什么呢?
其实这个在路上捡到的贝拿在手里也无所谓,最怕的是把它拿在心上。只要视所得为无所得,自然也会视所失为无所失。“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
结语:得,在路边捡到的贝。因为有所得,所以有所失。
悟
“悟”的构成元素是心和吾,吾就是我。
如果只把目光停留在结构上,那么这个“悟”是静态的。心与我紧密相连,失去心,我何以独存,失去我,心又何以谓心?心,是我的心;我,是心的我。
心与我犹如镜子的两面,本心是真实的,我相则是心的一种影像。冲破我相的大我,其实又是与心合二为一的。
如果我们撕开结构的樊篱,就会发现“悟”更是动态的。动态的“悟”是两个相互的方向和路径,要寻找真我,我们只有走进自己的心灵;要寻找心灵,我们只有打开自我。心是什么,心中的真我又是什么?佛告诉我们,是佛。
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诗偈:
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
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去灵山塔下修。
原来这个“悟”字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神秘的捷径。
我们为什么一生都在困惑,因为我们始终找不到自己的心灵。我们为什么一生都有无穷的烦恼,因为我们始终找不到心灵中的自己。
我们在世间找,在众生的目光中找。我们活给别人看,活给自己看,拼命地想从地位和荣誉中获得愉悦,然而尽管为此劳累一生,却从未体验过我们想得到的快乐。
我们在出世间找,奔波在通往西方世界的路上。参禅打坐,苦研佛经,然而一路上却把所有的亮光都误认为是指路的佛灯,一次又一次走在歧途上。只因为不肯转过头来,结果什么也找不到。
我们的心究竟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我们的旁边,只需要转过头来,就是悟。
我们心中的真我究竟在哪里?跨进心灵的门槛,迎面撞上的就是“我”。用揭去六尘的心眼来看“我”,就是悟。
悟,原来很简单。
结语:悟,我们的心就在我们的旁边。转过头,便可立地成佛。